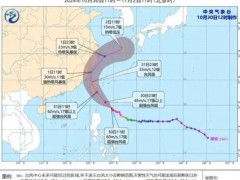2月12日,大年初三,在传统习俗里这一天又被叫做“小年朝”,人们有“不扫地、不乞火、不汲水”的习惯,以休息为主,好缓解一下前几日拜年守岁的疲惫。

在这样一个应该“睡到饱”的日子,62岁的曹在心却早早地启程,踏上了从河南老家返回深圳的路程。龙年春节,虽然其所在单位难得放假放到大年初八,但为了多赚几天工钱,曹在心还是选择提前回到深圳开始上班,
2024年已经是他“深漂”的第39年,从流水线工人、建筑工人、餐厅服务员、货车司机再到滴滴司机,作为深圳第一代农民工,曹在心基本将这座城市里常见的一线劳动岗位干了个遍。这39年,他看着自己的称呼从“小曹”慢慢变成了“老曹”,养育着自己的儿子成家立业,经历了家中老人的离世,眼下的他,工作岗位是深圳宝安一家物流园区里的门卫。
在曹在心眼中,门卫是一个非常合适自己的工作,不需要干什么重活,能在花甲之年找到这样一份清闲且一个月能有四千多元收入的工作,曹在心非常知足。
但说起来,他很羡慕与自己同岁、同乡且在同一个物流园区上班的赵永听。
“老赵身体好啊,他现在还能干搬运工,我现在腿脚不好干不了重活,他扛大包一个月最少八千多,干得多有一万多。”曹在心说。
初见赵永听时,记者很难相信这是一位已年过六旬的老人,他的身体异常健壮,肌肉线条分明。在物流园区干搬运工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动辄数十斤的货物,赵永听一把就能扛在肩上搬运进货车里。
“没学问只能干体力活,没什么可骄傲的。”在记者夸赞赵永听身体好时,他笑着跟记者说。
曹在心和赵永听都非常珍惜自己的工作,在应该退休的年龄,还能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很难得。
“六十多岁工作很难找的,人家看你年纪大都不要你,能有老板愿意给你份工作不容易。”赵永听说。
他们二人似乎都没意识到的是,按照我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像他们这样年满六十周岁且连续工龄满十年的男性劳动者,已经符合退休标准,理论上应该到了领着退休金,在家颐养天年的日子。
然而,当记者问及两位老人何时考虑办理社保退休手续,领上养老金回家休息时,曹在心和赵永听却都告诉记者,自己从来都没交过社保。
像曹在心和赵永听二人一般,于上世纪末南下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在深圳还有很多,他们如今都基本到了法定退休年龄。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深圳60岁及以上人口为940716人,占5.3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565217人,占3.22%。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提高2.36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提高1.39个百分点。深圳市民政局曾表示,预计到“十六五”时期,深圳将步入老龄化社会。
这些接近甚至是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又缺乏社会保障的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建设者,在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后,如何拥有一个体面的晚年生活?这正在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话题。
对社保“没概念”
在同赵永听和其工友接触的过程中,记者注意到一个普遍现象,像他们这样年龄在50岁至65岁的农民工,由于自身受教育水平及认知限制,对劳动者应当缴纳社保这一基本义务,并没有清晰的概念。
2000年,赵永听夫妻二人从河南省漯河市南下来到深圳打工。
直至今日,深圳市宝安区的福永街道与松岗街道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聚集地,在彼时,大量的港资、外资制造业的涌入,为当地提供了海量的基层劳动岗位,打工仔、打工妹正是曾经深圳乃至珠三角的热词。
来到深圳后,赵永听夫妻二人很轻松地进入到一家位于深圳福永的港资工厂里上班,据其回忆,2000年前后在深圳做普工,一个月收入在一千多元左右,看起来很低,但相较于在家乡务农,这已经是相当高的收入了。
为了省钱,初到深圳赵永听甚至没有租一个像样的房子,而是在宝安当地的城中村农民房里,找了一处阳台,以一个月一百多元的价格,夫妻二人蜗居在阳台里。
“房东都没见过这么租房子的,但他人挺好的,最后还是同意了,给我们把楼道里的阳台一封,装个门,我们就住阳台里。”赵永听说。
阳台蜗居的生活,一过就是十年。2010年前后,因为换了工作地点,赵永听才“恋恋不舍”地从阳台搬出来,在龙岗附近租了一个小单间。
夫妻二人之所以节衣缩食、省吃俭用地拼命挣钱,无外乎为了孩子。赵永听育有一儿一女,他们的孩子在河南老家由老人抚养,每个月,赵永听都会把绝大多数的工资汇给家中老人当生活费。
对自己在深圳的生活,赵永听很知足,一点也不觉得“苦”:“儿子结婚,家里盖了房子花了二十来万,不出来打工,哪来的钱盖房子?”
在此背景下,赵永听对工作和企业主的认知很简单——“用劳动换钱”,而对于企业主需要为其缴纳的社会保险,赵永听直到2008年前后,才第一次有了概念。
彼时,他想把自己孩子接来深圳生活,但是他在咨询了当地的公立学校后,发现自己的小孩没有办法在深圳办理入学手续。
“我们不是本地的,小孩户口都在河南,外地人的话,小孩上公立学校要社保,还要交够一定时间,我们从来没交过社保,也不知道上哪儿交。”赵永听告诉记者。
从某种程度上讲,赵永听算是亲历深圳发展过程的一线建设者,早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深圳“本地人”,但其在深圳工作的二十余年间,却一年社保都没有交过。
没交社保的原因,在2008年之前,是因为赵永听根本就不知道国家还有社会保险这一制度,而在2008年之后,则完全是由于其个人认知不足导致的。
曹在心甚至认为,交社保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在大公司才能享受的一项“福利”。“我们没什么文化,进不了大公司,坐办公室的大学生才能有社保。”曹在心说。
另外,嫌“交社保没用,麻烦”也是促成其放弃缴纳社保行为的重要原因。因为,在赵永听眼中,交社保不是一项福利,而是一项成本。
“要交社保的话,每个月要少拿很多钱,那东西交了又不让取,为什么要交?”在与记者讨论社保话题时,赵永听曾如是反问记者。
并非个例
像赵永听与曹在心二人一样,从未缴纳过社保的情况,在深圳第一代农民工这个群体里十分常见。
“我的老乡,我这些年换这么多工作,身边没几个交社保的。”曹在心告诉记者。
在这当中,除了有农民工自身对社保制度认知不清晰的因素外,企业主对为劳动者缴纳社保义务的“漠视”,也是一层不可忽视的原因。
时至今日,不少深圳的中小民营企业,并没有为员工提供缴纳社保这一选项。在曹在心于深圳工作的39年间,换过大大小小数十份工作,这些工作在岗位上各有不同,但唯一的共同点是都不会主动为员工缴纳社保。
“你去应聘,体检合格,拿个身份证就入职,上班干活人家给你开工资,从来没说过要缴社保这回事。”曹在心告诉记者。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了曹在心上一家工作单位的信息,这家在曹在心口中拥有一百来号员工的制造企业,2022年年报披露的参保人数竟然为0。
赵永听倒是遇到过愿意为其缴纳社保的企业,但该企业亦只是与其协商是否愿意缴纳,而非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强制缴纳。
“公司会问你要不要交社保,然后开的工资是交社保的一个价,不交社保的是另一个价,要是交社保每个月就少点钱,然后还要办很多手续,很麻烦,如果不愿意交就签一个协议,自愿放弃社保缴纳,我们很多人都会签。”赵永听说。
在采访过程中,赵永听和曹在心二人都不觉得企业未为其缴纳社保,是一件损害他们自身权利的事情。
“出来打工要求那么多,哪个厂都不会要你。”曹在心跟记者强调。
此外,站在民营企业的角度看,不为员工缴纳社保也是一种为提升企业效益而做出的“妥协”之举。宝安一家小型民营企业的负责人就告诉记者,缴纳社保对于小型民营企业来说,意味着不小的成本,如果全员缴纳社保,必然会大大增加企业的经营压力。
回农村种地
在完全没有缴纳过社保的情况下,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的曹在心或者赵永听对自己的退休生活有何打算呢?
对于这一话题,赵永听显得非常乐观。他告诉记者,自己并不是没有保障,其在河南老家很早就已经参与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新农合将会成为其退休后重要的生活保障。
“人老了不就是怕自己得病连累孩子吗?老家那边我很早就交了新农合,每年是380元,家里很多亲戚看病都用新农合报了不少,少花很多钱。”赵永听告诉记者。
而谈论起退休,曹在心则直接向记者表示:“我还这么年轻,退什么休。”
按照曹在心的想法,只要他还能找到工作,他就会一直在深圳打工,如果有一天年纪实在太大没有人要,他还会继续在深圳打零工,哪怕是“拾荒”,他都会一直坚持在深圳生活下去。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曹在心和赵永听二人,目前都没有在深圳购置任何房产,曹在心目前居住在公司提供的宿舍里,而赵永听仍是租房居住。
曹在心认为,当自己哪一天在深圳的生活成本大于收入时,自己才会选择回到老家生活。“挣不来钱的时候就退休。”曹在心说。
在记者问及没交社保,领不了退休金该如何保障晚年生活的话题时,赵永听提供的解决方案很简单——“回农村种地”。
赵永听亦告诉记者,他的晚年并不依靠退休金保障,其现在手里有三十余万的存款,足够他在河南老家过完余生。
“说难听点,只要不得什么大病,比如癌症之类的,就这么些年打工攒的钱,在家里,花两辈子都够了。”赵永听说。
曹在心曾经托人咨询过缴纳社保的问题,彼时他得到的答复是,非深户未参保人员达到退休年龄时,可能需要一口气补缴15年,方能按深圳办法领取养老待遇。
“补缴15年,要十来万块钱,而且还有一些要求,我不愿意掏这个钱,太多了,而且我也不符合条件,补缴不了。我补缴那么多钱,不就相当于自己给自己发养老金?跟用自己的钱也没区别。”曹在心告诉记者。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注意到,曹在心和赵永听二人对于自己的晚年生活都非常乐观,他们都不认为像自己这样的农民工兄弟的养老,会成为整个社会的问题或者负担。
“辛苦一辈子,我们一不给儿女添负担,二不给国家添负担,我们有手有脚,闲不下来,不需要退休金养老金,农民都是这样一代代过来的,没听说过领不到退休金,老了就吃不上饭了。”曹在心跟记者说。
“义务”和“权利”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其曾在调研过程中发现许多类似现象,企业主与员工签订了自愿放弃社保缴纳的相关协议。但从法律的视角来看,这类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通过沟通签订协议,放弃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是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要求的,在法律框架内,签订放弃社会保险义务的协议,本身就缺乏法律授权。
“社会保险的缴费本身是一种法定义务,无法通过民事关系解决。从法律角度来看,社会保险法所建立的社会关系或者社会保险权利,优于民事关系,这是国家强制制度安排,不可以通过自行协商方式解决。”鲁全说。
“深圳第一代农民工养老难的现象确实存在,例如农民工退保的数量很多,其次农民工没有按照实际工资缴纳,而是按照社平工资或者下限缴费,甚至未缴纳社保。但是,养老金制度具有长期性,保险制度都是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当你的义务未充分履行时,肯定无法充分享受权利,所以对于这类情况,在社会保险层面,无法解决。”谈及深圳第一代农民工社保缴纳不充分的现象,鲁全向记者分析指出。
“养老保险制度与其他制度不同,需要有长周期的视角。长周期需要20年或者30年缴费,这都是义务。你在缴费20年至30年之后退休才可以享受权利,你的义务履行状况和缴费程度决定你的权利享受程度。目前这一批农民工的养老状况相对较差,但我们不能在养老保险制度中寻找解决办法,如果他们没有缴费,(社保)就多给他们一些,这个制度的基本规则就被破坏了,所有人都会认为现在少缴一点,未来都能拿到。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国民养老保险教育。”鲁全称。
在鲁全看来,类似曹在心和赵永听这类农民工的退休生活保障,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寻求解决方案。
“第一代农民工已经回到农村,实际上不用担心,他们多年的积蓄已经足够支持晚年生活,但我们要防止出现问题,出现极端事件,比如,退休农民工的生活水平或者养老金水平低于当地低保标准,养老金是退休农民工的唯一收入来源,那可以用低保制度进行弥补。所以,第一,不能破坏养老保险制度的规则;第二,是需要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持。如果你在保险制度中无法获得保障,那么就应该由基本救助制度去发挥作用。”鲁全如是说。